人民得安居 畢生情所系
——記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吳良鏞院士
●記者 程曦 實習記者 于帥帥 趙姝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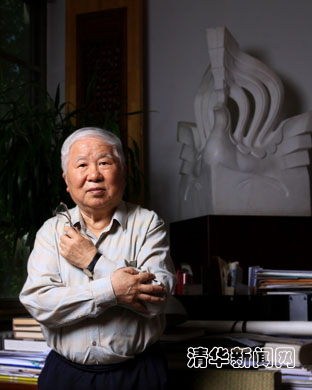
圖為吳良鏞院士。
我畢生追求的就是要讓全社會有良好的與自然相和諧的人居環(huán)境,讓人們詩意般、畫意般地棲居在大地上。
——吳良鏞
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有錦繡山河,也有巍峨城郭。中國人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災難與建設無數(shù)次改變了它的面貌。
這片土地會記住這樣一位老人:他用近70年的時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探索中國建筑與城鄉(xiāng)規(guī)劃的發(fā)展道路,為新世紀人居環(huán)境建設指明了方向。
歲月和疾病使他的腳步不再像當年那樣迅疾、矯健,卻擋不住他探索的激情。年屆九旬的他依然活躍在學術舞臺上,為締造和諧社會與美好人居環(huán)境而辛勤工作。
他,就是我國著名的建筑與城鄉(xiāng)規(guī)劃學家、建筑教育家,人居環(huán)境科學的創(chuàng)建者,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吳良鏞。
2012年2月14日,他從國家主席胡錦濤手中接過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證書。
這是中國科技界的最高榮譽。這本殷紅的獎勵證書,承載著祖國和人民對他畢生探索的真摯謝意與崇高敬意。
苦難中迸發(fā)的建筑夢
20世紀上半葉,中國大地戰(zhàn)火紛飛,吳良鏞的成長歷程中飽含著流離失所、國破家亡的民族血淚,這促使他義無反顧走上學習建筑的道路。少小時被典當人威脅要揭走屋瓦,不得不帶著傷寒高燒的妹妹告別祖居;日軍鐵騎逼近南京,加入逃難者隊伍的他從此開始顛沛流離;大學入學考試最后一科剛剛結束,轟炸機的陰影就降臨合川,死傷無數(shù),毀掉半座城池的大火直到次日還在熊熊燃燒。青年吳良鏞背井離鄉(xiāng),目睹國土的淪喪,層層累積的苦難激發(fā)了他重建家園的熱切愿望。1940年,他走進了中央大學建筑系。
1943年,在中央大學圖書館的暗室里,吳良鏞看到了一批越過“駝峰航線”運來的國外建筑雜志縮微膠卷。他驚訝地發(fā)現(xiàn),同樣飽受戰(zhàn)亂侵擾的西方,建筑界并不是無所作為,而是信心百倍地放眼未來,致力于戰(zhàn)后城市重建和住宅建設的研究。國破山河在!戰(zhàn)后重建的美好愿景如同一道劃破黑夜的閃電,照亮了這個建筑學子的心。
1946年抗戰(zhàn)勝利后,剛畢業(yè)兩年的吳良鏞應梁思成之邀,協(xié)助他創(chuàng)辦了清華大學建筑系。建系之初,梁思成赴美講學,吳良鏞和梁思成夫人林徽因成為系里最初的兩名教員。1948年夏,梁思成推薦吳良鏞去美國匡溪藝術學院深造。在世界著名建筑師沙里寧的指導下,吳良鏞開始探索中西交匯、古今結合的建筑新路,其間曾獲羅馬獎金建筑繪畫雕塑設計競賽榮譽獎,在美國建筑界嶄露頭角。
重建家園的創(chuàng)造與困惑
新中國成立后,梁思成、林徽因給吳良鏞寄去了一封信。信中表達了對祖國重獲新生的喜悅之情,希望他趕緊回來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百廢待興”,這四個字讓吳良鏞迅速作出明確的抉擇。1950年底,和那個時代許多充滿赤子情懷的科學家、藝術家一樣,吳良鏞沖破重重阻撓,繞道歸來,投身新中國的建設和教育事業(yè)。作為新中國建筑教育和建筑事業(yè)的開拓者之一,他于1951年開始主持清華建筑系市鎮(zhèn)組工作,并與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汪菊淵教授一道創(chuàng)辦了我國第一個園林專業(yè)。1952年起,吳良鏞歷任建筑系副主任、主任,全面推動建筑技術科學、建筑歷史與文物保護等學科的發(fā)展。
1959年,吳良鏞倡導創(chuàng)辦了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在此前后,他還曾主持全國建筑會議、制定共同教學計劃,參與領導全國建筑學專業(yè)通用教材的建設,并主持《城鄉(xiāng)規(guī)劃》教學用書的編寫。他是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顧問和保定、北戴河、秦皇島、邯鄲等城市的規(guī)劃建設顧問;人民英雄紀念碑、北京圖書館等著名建筑都曾凝聚他的心血;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余震未消,他就作為最早一批專家參加重建規(guī)劃。
舊中國民生凋敝的影像在一批批拔地而起的新建筑、一座座百廢俱興的新城市身后漸漸淡去,吳良鏞的心頭卻縈繞著越來越深的困惑:20世紀40年代初,他抱著希望避免西方“城市病”的愿望開始學習城市規(guī)劃,回國后也曾相信中國城市可以完全避免交通擁擠、住宅短缺、破壞自然等現(xiàn)象。然而,數(shù)十年間中國城鄉(xiāng)變化雖巨,現(xiàn)實面貌卻似乎和這一理想呈現(xiàn)出較大偏差。在曲折中,吳良鏞蓄積力量、摸索前進,新的變革契機正在下個路口轉(zhuǎn)彎處等待著他。
時代激流中的探索
1980年,吳良鏞成為文革后第一批當選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改革開放的春風中,各項事業(yè)蓬勃發(fā)展,各門學科也開始了新的探求。從西德講學歸來的吳良鏞參加了1981年的中科院學部大會,他深深感受到全國學術界探索未來的高昂熱情,感受到當代建筑學家對建筑學科發(fā)展所應肩負起來的重任。
“這次大會使我認識到,面對新中國成立與文革后的經(jīng)驗與教訓,建筑學要有所作為就必須走向科學,向建筑學的廣度和深度進軍。”為了求解這條建筑的科學發(fā)展之路,年逾花甲的吳良鏞抖擻精神,從理論與實踐兩個維度同時進發(fā)。
在理論上,吳良鏞從20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進行“廣義建筑學”的思考,并于1989年出版了專著《廣義建筑學》。其著眼點從單純的“建筑”概念轉(zhuǎn)向“聚居”,“從單純的房子拓展到人、到社會,從單純物質(zhì)構成拓展到社會構成”,大大拓展了建筑學的視野。事實上,廣義建筑學已經(jīng)在很大程度上將“廣義的住”、“空間環(huán)境”、“多學科綜合研究”等思想從理論上結合起來,形成了后來人居環(huán)境科學思想的雛形。
在積極探索理論的同時,吳良鏞還和同事們一起踏遍千山萬水,為解決中國城鄉(xiāng)建設的實際問題,完成了一項又一項貢獻重大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
20世紀80年代初在吳良鏞指導下完成的“北京奧林匹克建設規(guī)劃研究”,就是其中較早的一項成果。針對當時已申辦成功的亞運會和未來北京奧運會的建設工作,他以“經(jīng)濟時空觀”思想為基礎,運用系統(tǒng)分析方法將項目策劃、項目運行和賽后安排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力圖以最少的投資取得最大的建設效果。最終提出集中與分散相結合的建設模式,以及按需修建比賽場館、建好的場館盡量做好賽后使用的銜接安排等建議。這些建議都得到了政府相關部門的關注和采納,該項研究獲得1987年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一等獎。
在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的今天再來看這項研究,我們更能體會到它的前瞻性:奧運會對場館設施建設的要求相比亞運會時已經(jīng)有非常大的提升,如果當時就把主場館蓋好了,如今只會成為尷尬的“雞肋”。拒絕“大而全”,結合實際留下發(fā)展空間,這一思想對北京的奧林匹克建設助益良多。
1984年4月底,62歲的吳良鏞卸去擔任多年的系主任職務。這年夏天,他在清華主樓9層的半間屋子里,帶領一名教師和幾名研究生,開始清華大學建筑與城市研究所的初創(chuàng)工作。
20世紀90年代初,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的長江三角洲地區(qū)吸引了吳良鏞的視線。東部這片肥沃豐美的土地已經(jīng)加速行駛在城市化的快車道上,城市規(guī)劃的思想、原則卻相對落后,發(fā)展中出現(xiàn)了種種尖銳的矛盾和問題。于是,他帶著助手幾下江南,在上海、蘇錫常和寧鎮(zhèn)揚三個地區(qū)進行了細致的調(diào)查研究,一次又一次撰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建議。
1992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首次將重點項目資助投放在建筑領域。在吳良鏞主持下,清華大學、東南大學和同濟大學聯(lián)袂開展“發(fā)達地區(qū)城市化進程中建筑環(huán)境的保護與發(fā)展”研究。這樣一個多單位、跨學科、多領域、綜合性的區(qū)域性研究,成為我國建筑和城市規(guī)劃領域的首次嘗試。
清華大學建筑與城市研究所主要負責蘇錫常地區(qū)的規(guī)劃研究。其間,吳良鏞對這一區(qū)域的發(fā)展和每個城市的規(guī)劃都做了認真考察和科學預測,并指導學生和助手完成了若干城鎮(zhèn)和縣域規(guī)劃,使研究呈現(xiàn)出城、鄉(xiāng)并重的豐富性和整體性。
這項長達5年的研究于1997年結題,它首次提出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觀念并注重保留與發(fā)揚地方建筑特色,贏得各方好評,獲得2000年中國高校科學技術獎二等獎。
社會學家費孝通主持進行了項目技術鑒定和結題驗收。這位改革開放之初以“小城鎮(zhèn)大問題”推動中國小城鎮(zhèn)建設的著名學者對這一項目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他們?yōu)樘K南小城鎮(zhèn)的物質(zhì)空間環(huán)境改善作出了貢獻。闊別故土半個世紀,吳良鏞終于在生養(yǎng)他的江南水鄉(xiāng)實現(xiàn)了一個久遠的夢想。
北京西北文教區(qū)和中關村科技園規(guī)劃建設、上海浦東規(guī)劃、廣州城市空間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深圳城市總體規(guī)劃和福田中心區(qū)規(guī)劃、三峽工程與人居環(huán)境建設、滇西北人居環(huán)境可持續(xù)發(fā)展規(guī)劃研究、南水北調(diào)中線干線工程建筑環(huán)境研究……在這一個又一個至關重要的實踐課題中,吳良鏞傾注了自己對吾土吾民的熱愛,奉獻了自己的才學與思想。他在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居環(huán)境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將一直為世人所銘記。
中國人居環(huán)境科學的奠基人
伴隨著理論和實踐探索的不斷深入,吳良鏞逐漸理解到,不能僅囿于一個學科而應從學科群的角度整體探討學科發(fā)展,因此提出了“人居環(huán)境科學”這個整合眾多學科的“學科群”概念。
1993年8月,在中科院技術科學部學部大會的學術報告中,吳良鏞(與周干峙、林志群共同撰文)提出“人居環(huán)境學”這一新的學術觀念和學術系統(tǒng)。
1999年,國際建筑師協(xié)會第20屆世界建筑師大會在北京召開,吳良鏞擔任科學委員會主席,作大會主旨報告,并起草《北京憲章》。《北京憲章》以人居環(huán)境科學理論為基礎,提出“建設一個美好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人居環(huán)境,是人類共同的理想和目標”,在大會上獲得一致通過。時任國際建協(xié)主席斯戈泰斯稱贊這是一部“學術貢獻意義永存”的文獻。英國建筑評論家保羅·海厄特認為吳良鏞以一種樂觀和利他主義的姿態(tài),提出了引導未來發(fā)展的“路線圖”。作為國際建協(xié)成立50年來的首部憲章,它成為指導新世紀世界建筑發(fā)展的重要綱領性文獻,并以中、英、法、西、俄5種文字出版。
2001年,吳良鏞出版專著《人居環(huán)境科學導論》,創(chuàng)造性地建構了中國人居環(huán)境科學的理論體系、學術框架和方法論,進一步奠定了中國人居環(huán)境科學的研究基礎。人居環(huán)境科學以人居環(huán)境為研究對象,是研究人類聚落及其環(huán)境的相互關系與發(fā)展規(guī)律的科學。它針對人居環(huán)境需求和有限空間資源之間的矛盾,遵循五項原則:社會、生態(tài)、經(jīng)濟、技術、藝術,實現(xiàn)兩大目標:有序空間(即空間及其組織的協(xié)調(diào)秩序),以及宜居環(huán)境(即適合生活生產(chǎn)的美好環(huán)境)。2010年,人居環(huán)境科學作為原創(chuàng)性重大科學技術成就獲得“陳嘉庚科學獎”,該獎認為:“人居環(huán)境科學理論針對建設實踐需求,尊重中國歷史傳統(tǒng)與價值,為中國大規(guī)模城鄉(xiāng)空間建設提供科學指導,……為世界人居環(huán)境建設提供指引。”
人居環(huán)境科學構建起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建筑學理論體系,它在建筑學理論上的重大意義毋庸置疑;而如果對吳良鏞主持的一系列重大科研項目進行一番回顧分析,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它們同樣是以這一理論體系為指導,并以其現(xiàn)實成就印證了人居環(huán)境科學理論的重要價值。
例如:自改革開放之初起,吳良鏞就一直在思考北京及其周邊地區(qū)發(fā)展的問題。直到1999年1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九五”重點資助項目——“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中國人居環(huán)境的基本理論與典型范例”正式立項,其主要課題即為京津冀地區(qū)城鄉(xiāng)空間的發(fā)展規(guī)劃研究。隨后,相關研究又先后得到清華大學985研究基金和建設部重點科研項目的支持。
吳良鏞以其個人聲望和課題的重大戰(zhàn)略意義動員了十多個單位、幾百位專家直接參與這一項目,組織了北京、天津、河北等兩省一市有關部門和不同專業(yè)的合作,利用多層次的溝通與交流,建立起“科學共同體”,在區(qū)域?qū)用婢唧w運用人居環(huán)境科學理論進行研究。研究確立了地區(qū)規(guī)劃的一些基本思路,如核心城市“有機疏散”與區(qū)域范圍“重新集中”的結合、明確劃定保護地區(qū)或限制發(fā)展地區(qū)、“交通軸+葡萄串+生態(tài)綠地”的發(fā)展模式等,無不體現(xiàn)出整體塑造區(qū)域人居環(huán)境的理念。
2002年研究報告發(fā)表后,北京市、天津市先后邀請課題組參加其空間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和城市總體規(guī)劃修編,并由吳良鏞擔任首席領銜專家。這一系列研究直接指導了北京近10年來的建設發(fā)展,面向城市蔓延、舊城保護乏力等問題,開創(chuàng)了新時期北京城鄉(xiāng)規(guī)劃的新局面。其中在舊城保護領域,提出舊城積極保護戰(zhàn)略,促進了從“大拆大建”到“有機更新”的政策轉(zhuǎn)變,從“個體保護”到“整體保護”的社會共識,北京舊城整體保護思想逐步達成社會共識。
現(xiàn)在,吳良鏞又帶領團隊開展了面向建國100周年、關于城市發(fā)展模式的研究——“北京2049”。建設學科群、打造跨學科平臺、開展多情景模擬……人居環(huán)境科學的思想理念和方法論在其中得到充分體現(xiàn)。
回顧吳良鏞的每一次研究,他總是努力走在時代的前面,“遠見于未萌,避危于無形”:在北京保護與發(fā)展的矛盾尚未完全暴露前,就主動開展區(qū)域整體的規(guī)劃研究;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提出三峽工程不是一個純粹的水利工程,而是人居環(huán)境一個大的變動,建議應對三峽人居環(huán)境建設予以及時關注、切實指導——時至今日,《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06-2020年)》已經(jīng)把“城鎮(zhèn)人居環(huán)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列為城鎮(zhèn)化與城市發(fā)展領域的三個戰(zhàn)略重點之一。
我們不妨提出這么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吳良鏞,沒有他所提出的這樣一個整合建筑、規(guī)劃與園林等學科,融貫科技、歷史與文化的人居環(huán)境科學體系為指導,今天中國的城鄉(xiāng)發(fā)展又會呈現(xiàn)出怎樣的面貌?
正如兩院院士、建設部原副部長周干峙所言:“吳先生通過總結歷史的經(jīng)驗和中國的實踐提出的人居環(huán)境科學,從傳統(tǒng)建筑學擴展到廣義建筑學,再到人居環(huán)境科學符合科學發(fā)展規(guī)律。如今我們的規(guī)劃設計工作已經(jīng)相互交叉、融會貫通、相互集成、多學科已經(jīng)聯(lián)系起來。實踐證明,這樣的融貫、集成避免了許多決策的失誤,所帶來的經(jīng)濟、社會和環(huán)境效益不可估量。”
矢志不渝的民生情懷
吳良鏞做過許多宏觀和中觀的戰(zhàn)略性規(guī)劃,但在1993年,他卻因為對北京胡同里一個四合院的改造項目獲得了“世界人居獎”與“亞洲建協(xié)建筑設計金獎”。
菊兒胡同是吳良鏞探索北京舊城保護與發(fā)展問題的一塊“試驗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帶領一批又一批研究生在這里進行調(diào)研和規(guī)劃設計。通過居民互助、政府資助、單位補貼等途徑,以及房改加危改的方式,當年破敗的“危積漏”(危房、積水、漏雨)院落變成由一座座功能完善、設施齊備的單元式公寓組成的新四合院住宅。擴展形成的“跨院”又突破了北京傳統(tǒng)四合院的全封閉結構,形成鄰里交往的嶄新空間。粉墻黛瓦、綠樹成蔭,氣象一新的菊兒胡同仍舊保持了與北京舊城肌理的有機統(tǒng)一。
這個項目規(guī)模不大卻費盡周折,凝結了吳良鏞的智慧和心血。建筑學院左川教授感慨地說:“對這個2760多平方米、僅一萬元設計費用的小工程,吳先生可以說是不嫌其小,又不厭其煩。”
選擇菊兒胡同,除了旨在為北京舊城建設探索一條道路,也體現(xiàn)了吳良鏞一以貫之的民生情懷。菊兒胡同的改建過程中,他特別關心原有居民的回遷情況;改建工程告一段落之后,他還多次派人回訪,一直關注著社區(qū)活動、綠地保護等工作的落實。
吳良鏞曾說:“一個真正的建筑大師,不僅看他是否設計出流傳百世的經(jīng)典建筑,而是看他是否能讓自己國家的老百姓居有定所。”“與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民居。民惟邦本,普通人的居住問題是建筑最本質(zhì)、最核心的內(nèi)容。”
每次外出工作,他總是有意識地到老百姓住的地方去看一看。在四川成都進行三峽工程與人居環(huán)境研究時,他還特地去“圩”(集市)上了解普通農(nóng)民的生活。在指導清華建筑學院住宅研究方向的發(fā)展時,他也特別強調(diào)要保持自己清醒的判斷和思考,在開展住宅研究時更多關注它的社會屬性,對住區(qū)和住宅發(fā)展的整體狀況進行調(diào)查分析,為行業(yè)的健康發(fā)展和國家政策的制定建言獻策。
培養(yǎng)人居環(huán)境“集團軍”
如果說上世紀中葉梁思成先生提出的“體形環(huán)境”思想為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創(chuàng)造了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教育建筑平臺,那么吳良鏞先生創(chuàng)建的人居環(huán)境科學則是新時期清華大學建筑學科的辦學指導思想。以此為基礎,奠定了清華建筑學院面向人居環(huán)境的“建筑學-城鄉(xiāng)規(guī)劃學-風景園林學”學科架構和教學體系。
自1946年協(xié)助梁思成創(chuàng)辦清華大學建筑系以來,吳良鏞歷任副系主任、系主任,建筑與城市研究所所長,人居環(huán)境研究中心主任,為清華建筑教育的發(fā)展傾盡心力。這60多年來,從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先后走出建筑領域院士9人(占全國總數(shù)的38%),國家勘察設計大師16人(占全國總數(shù)的30%),國內(nèi)外知名建筑學院院長和國際知名學者33人,國有大型設計單位院長、總建筑師、總規(guī)劃師65人。清華建筑學專業(yè)的學科整體水平始終在全國保持領先。
作為導師,吳良鏞親自培養(yǎng)了81名博士和碩士研究生,“一把鑰匙開一把鎖”是他廣為人知的育人理念。每個學生開題時,他都要針對學生的特點和興趣仔細琢磨,和學生一起討論合適的題目。
對于在職的論文博士,吳良鏞每年都要召集至少兩次以上的學術例會,請來自全國各地的論文博士交流他們的研究進展。在這樣的學術例會上,每個人的選題都經(jīng)過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復打磨修改。
他對學生要求極嚴,但也充滿關愛。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吳唯佳至今記得20多年前的一個雨夜,吳良鏞披著雨衣沖進他在三號樓的宿舍,了解他的學習情況和需求的情景。還有一位博士生曾滿懷深情地這樣寫道:“我無法忘記吳先生帶著我作的一次古都之行。他這么大的年紀,領著我從北京古城的景山到什剎海,在蔥蔥綠蔭的胡同里穿行,還買了一塊特別好吃的燒餅讓我品嘗。那一刻,我深知他心中巨大的愛,我對這個城市的愛也被他點燃。”
吳良鏞提倡讓人才在集體“大兵團戰(zhàn)斗”中成長。每一個研究和實踐項目,都是他培養(yǎng)人才的平臺。但是,他特別強調(diào)做項目不能像“炸油餅”,盲目進行生產(chǎn)性的重復勞動,而是要在整個集體共同的學術框架下進行,成為從科學進步和創(chuàng)新出發(fā)的“作品”。
清華大學常務副校長陳吉寧認為:“人居環(huán)境科學的發(fā)展極大拓展了傳統(tǒng)建筑學的研究領域,帶動了建筑、規(guī)劃、環(huán)境、市政、景觀、生態(tài)和地學等多個學科的發(fā)展,推動了不同學科之間的融合,為解決人類當前快速城市化、工業(yè)化進程中的空間可持續(xù)發(fā)展問題提出了新的理論指導。在一流大學建設中,如何以國家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為舞臺,創(chuàng)新學術思想和理論,吳先生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典范。”
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建筑學院教授鄧衛(wèi)欽佩地說:“吳先生最大的貢獻,一是適應時代需要,勇于理論創(chuàng)新。他在充分吸取前人理論貢獻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當前大規(guī)模、高速度的城鎮(zhèn)化的時代背景,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人居環(huán)境科學理論,為建筑學的科學發(fā)展指明了方向;二是面向重大問題,探索實踐模式。通過區(qū)域、城市、街區(qū)、建筑等不同層次的實踐探索,他為在中國城鄉(xiāng)建設中實現(xiàn)美好人居理想找到了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方法和道路;三是堅持融會貫通,引領學科發(fā)展。他在相關學科融會貫通的基礎上搭建起人居環(huán)境科學這個共同的平臺,使建筑學領域內(nèi)各學科的協(xié)同創(chuàng)新成為可能。從這一點來說,他是獨一無二的。”
“少有的刻苦、激情和堅強”
1948年在吳良鏞赴美留學前夕,林徽因讀到梁思成寫好的推薦信后,又提筆增添,“少有的刻苦、淵博,少有的對事業(yè)的激情,多年與困境抗爭中表現(xiàn)出的少有的堅強”。
這的確是對吳良鏞奮斗精神的一個傳神寫照。
曾經(jīng)有很長一段時間,他總是在清晨最靜謐的時刻起身,抓緊時間進行學術研究工作,白天再處理繁雜的日常事務。
曾擔任吳良鏞科學秘書的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武廷海回憶說,起草《北京憲章》時,經(jīng)常在凌晨2點多,他把按吳良鏞批注修改好的材料騎車送到吳家門前的小報筒,4點多鐘吳先生就會起來工作,開門取走材料進行再修改,精益求精。
2008年夏天,吳良鏞不顧南京炎熱的氣候,堅持在金陵紅樓夢博物館的工地上現(xiàn)場指導,結果由于天氣炎熱、出汗過多而突發(fā)腦梗,先在天壇醫(yī)院搶救,再住進康復醫(yī)院治療。
在天壇醫(yī)院,面對前來探望的學院教師,他的第一句話不是談論病情,而是吃力卻堅定地說:“奧運會馬上就要召開了,在奧運期間調(diào)查首都北京的城市空間狀況是千載難逢的大好良機,不要耽誤,一定按照之前布置好的做下去,把調(diào)查做好。”聽到這句話,在場的教師既意外又感動:先生全身心為事業(yè)投入的精神,是一般人難以望其項背的。
那段時間,病床就是他的辦公桌。雖然身體不能動,可他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對手頭所有工作的關心:通過口授安排南京工地的工作,思考《中國人居史》的研究,聽取研究生課題進展的匯報……
時年86歲高齡的吳良鏞,還以驚人的毅力進行身體康復訓練。酷熱的夏天,他穿著小背心,每次做完康復訓練,衣服全濕透了。在醫(yī)院里,他還開始練習用左手寫字,右手的功能也通過按摩和訓練一點點得到恢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出院時他送給醫(yī)護人員的答謝禮竟是一幅漂亮的書法。對于一個剛剛從中風狀態(tài)恢復過來的耄耋老人,這是多么的不易!建筑學院邊蘭春教授深有感觸地說:“只有在那個過程中親眼見證他每一點變化的人,才能真正體會到吳先生的毅力之強大。看到這些,也就為他在事業(yè)上的堅持找到了一個注腳。”
現(xiàn)在,吳良鏞又重新投入到高密度的工作中。同事們給他制定了保護身體的“八項注意”,他一般總是盡一切可能身體力行,有時也不免“巧妙迂回”。
活到老,學到老。學養(yǎng)深厚令人嘆服的吳良鏞,至今依然敞開胸懷吸納一切有益的思想,孜孜不倦地探索新知。最近熱銷的《喬布斯傳》,也進入了他的閱讀視野。吳良鏞認為喬布斯有自己獨特的方法論,這使他很感興趣,想看看是否能從中獲得借鑒,對學問有所裨益。
吳良鏞為全校研究生開設《人居環(huán)境科學導論》課程,多年來他堅持親自做開課和結課演講,只有2008年生病時缺席了一次開課,到年底,他還是拄著拐杖從康復醫(yī)院走上了講臺。
2011年12月27日,是最近一次結課演講的時間。面對臺下那群滿懷熱切目光的年輕人,他回顧了自己從對建筑學產(chǎn)生困惑到完成幾次“頓悟”、發(fā)展人居環(huán)境科學的全過程,談到了對這門學問向“大科學、大人文、大藝術”融匯發(fā)展的期待,也回憶起抗戰(zhàn)時在茶馬古道上感受到的風土人情和人民疾苦,以及由此對那里的建筑、那里的百姓所抱有的特殊情感……這一講,就是兩個多小時。
在這次演講中,吳良鏞懇切地評價了自己所創(chuàng)立的人居環(huán)境科學:“人居環(huán)境科學提出后,進行了一定的理論和研究的構建,并且已經(jīng)進行了融貫區(qū)域、城市、建筑等多種層次的實踐,但仍舊要不斷地完善、展拓。它是一個開放的巨系統(tǒng),到現(xiàn)在并沒有定型……我們不過點燃了一根小小的蠟燭,熱情地期待后繼者發(fā)揚光大,使之普照大地。”
手擎這支明燭,90歲的吳良鏞依然孜孜不倦,行走在通往夢想的道路上。
編輯:欣 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