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晴:“承續(xù)清華文脈是我的責任”
研通社記者 曾 點

李成晴,男,清華大學人文學院2009級碩士生、2012級博士生,師從謝思煒教授,研究方向為唐宋文學與文獻,2009年由蘭州大學保送清華大學讀研。在攻讀博士期間,李成晴以獨立作者身份錄用和發(fā)表高水平論文20余篇,其中包括《文物》等權(quán)威期刊2篇,《文獻》等CSSCI論文21篇,日本《白居易研究年報》等國際期刊3篇。李成晴志在秉承清華文史傳統(tǒng),致力于中古寫本文集的研究,學術(shù)旨趣是從文史、文獻、文物相結(jié)合的角度對文本個案進行釋證。他曾獲2012年清華大學博士研究生新生獎學金、研究生國家獎學金(2014、2015年連續(xù)兩年)、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獎學金等獎項。
大師未竟的研究,他在接著做
顧炎武曾在《日知錄》中論著書說:“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無,而后為之。”大師沒有走完的路,需要后來者接著往前走。在學術(shù)研究的道路上,專注于唐代寫本文獻學研究的李成晴,用自己的選擇踐行著這一點。他以這樣的方式,承續(xù)清華人源遠流長的學術(shù)傳統(tǒng),向遠去的大師致敬。“寫本文獻學的研究確實特別冷門,但是,對于我來說,這是一種責任”,李成晴微笑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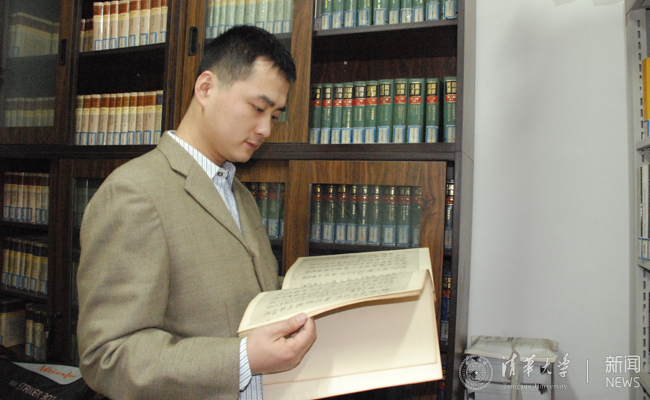
李成晴在閱讀古籍。
將近一百年前,世人的眼光都被敦煌所震驚,以敦煌新發(fā)現(xiàn)的中古文獻為基礎,新生的寫本文獻學研究成為了“顯學”,風靡一時。陳寅恪、王國維等先生開創(chuàng)的學術(shù)研究范式,到今天不僅沒有過時,反而會在E考據(jù)時代被賦予了新的意義。
“我曾經(jīng)認真思考過,為什么陳寅恪先生在《論語疏證序》等多篇文章中都強調(diào)合本子注這一體例對著作撰述的影響”,李成晴說。他的理解是,要對古人學術(shù)有一“了解之同情”,需要先明瞭古人著述的義例:知其例之源流正變,則解說論斷才可能得其要領。正是在這樣的認識下,李成晴在研究中對中古文集的義例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文獻學的研究關(guān)鍵在于資料,而資料的獲取需要研究者付出巨大的努力。在李成晴的研究中,除了已經(jīng)影印的敦煌文獻,同樣需要的還有日本所藏的古抄本和海外宋元刻本文集,而這些文獻材料大都是收藏機構(gòu)的鎮(zhèn)館之寶,不但很難目睹真容,連獲取照片或影印件的難度都特別大。即使委托師友前去查閱,也只能帶鉛筆抄寫而不能拍照。
在寫本文獻學的研究者眼中,沒有原件影像就意味著無法開展研究。雖然研究面臨著重重困難,李成晴卻沒有放棄。機緣巧合的是,他的導師謝思煒先生與日本學界多有學術(shù)交往,從而幫助他查閱了很多珍貴的文獻資料。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可以說,李成晴現(xiàn)在所做的研究正是陳寅恪先生和王國維先生這些老一輩清華學人工作的延續(xù)。
祖父的銅范,最初的啟蒙
2002年,正在讀高中的李成晴,非常偶然地在舊書攤上看到了一部線裝的《淄川縣志》,標價三百塊。雖然對于十三年前的一個高中生而言,三百塊無疑是一筆巨款,李成晴卻思考再三決定把它買了下來。當時的他絕對不會想到,十幾年后的今天,文獻學研究已經(jīng)成為了他終生追求的學術(shù)事業(yè)。
除了這次與古文獻的親密接觸,從小就深受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也是推動李成晴走上文獻學研究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這個過程中,他的祖父足以稱得上是他的“引路人”,盡管這個“引路人”也只是曾經(jīng)接受過幾年私塾教育而已。“祖父最初教我寫字用的銅框,我現(xiàn)在都珍藏著,小時候的寫仿,讓我感受到了傳統(tǒng)書法對每一個漢字的敬重”,李成晴接著說:“當然,就學術(shù)研究而言最初形成的興趣只是一個方面而已。”
的確,學術(shù)研究與文史愛好并不是一回事,學術(shù)研究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付出。如果沒有特殊情況,每天清晨的七點,李成晴必定已經(jīng)坐在了人文學院古文獻中心的辦公室里。接下來的一整天時間,他都將埋頭于這里海量的文獻資料。周末兩天也被他全部用來整理這一周所取得的研究進展。他深知學術(shù)研究更多的要依靠長時間的積累,只有日積月累,才能厚積薄發(fā)。在李成晴的書架上,筆者看到了一冊冊各自命名的札記冊:《并蒂桃齋日課》、《雀窗筆記》、《待仁齋椾札》、《林樓筆記》……在攻讀碩士和博士的這七年時間里,他的讀書筆記和資料整理已經(jīng)超過了300萬字,而所有寫過的論文加在一起也已經(jīng)超過了60萬字。

李成晴所作的讀書筆記。
正是這種超乎常人的付出使李成晴能夠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2015年可以說是他在進入專業(yè)研究領域后的豐收之年。截至11月,被發(fā)表或錄用的核心期刊論文就已經(jīng)超過了十篇,當然,其中的許多論文都是在資料長編的積累過程中慢慢找到問題發(fā)生點的。
是學者,更是丈夫、兒子、父親
“其實挺慚愧的”,談到自己的家庭,李成晴顯露出幾分歉疚:“沒有她們的陪伴和理解,我就不可能這么多年守著一張安靜的書桌。”在古文獻中心,這個文質(zhì)彬彬的山東漢子是一個專注于文獻學研究的學者;但是在自己家里,他集丈夫、兒子和一個一歲女孩的父親三重身份于一身。繁忙的科研使他沒有太多時間陪伴家人,比如,常常只能是在午餐之余逗逗尚在襁褓中的女兒。
對于家人而言,他選擇走學術(shù)研究的道路就意味著讓她們等待,因為漫長的求學生涯把圍爐夜話式的安居樂業(yè)推向了未來。雖然如此,妻子和雙方父母仍然堅定地支持他做他自己喜歡的事情。兩年前,李成晴的母親為了照顧他懷孕的妻子來到了北京,現(xiàn)在又在幫他照顧女兒。生活盡管平淡,整個略顯擁擠的屋子里卻始終暖意融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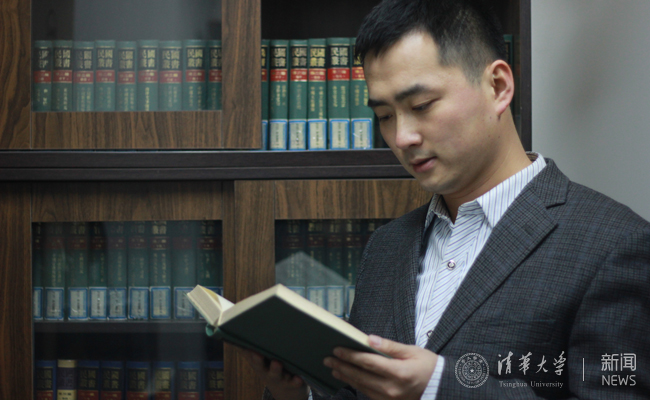
李成晴在書房中。
李成晴也總是以各種可能的方式表達著他對家人的無限愛意。清華園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滿了故事,更是被融入了詩情畫意。幾年前,李成晴按照自己對清華草木的理解,撰寫了一本《清華水木譜》,《引言》中寫道:“予負笈北來,觀書之暇,常與內(nèi)子書倩閑步園中,對菊聯(lián)詩,臨波懷往,悠悠數(shù)年矣。”這個他與妻子共同漫步清華園的畫面極其浪漫,而他與妻子之間的情真意切也在字里行間躍然紙上。
有了家人支持,李成晴在學術(shù)研究的道路上更加篤定。不僅在具體的學術(shù)問題上做出了許多成果,在治學方法上更是取得了巨大突破。《文物》雜志審稿專家認為,李成晴拓寬了文史考證的視角,能夠借助文獻、文物的制度研究,探討文史問題,屬于研究方法上的新創(chuàng)獲。李成晴的代表作《故宮博物院藏<宋賢四帖>考》采納的就是這種研究方法。
李成晴很欣賞章學誠的一句話:“夫?qū)W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高中時代閱讀過的《談藝錄》和《陳寅恪詩集》,如今已經(jīng)化為他學術(shù)思考的底色:“人身難得,此生既然認定了學術(shù)研究的意義,就要在行動上像兩位先生那樣勇猛精進”。
供稿:研通社 編輯:常 松
